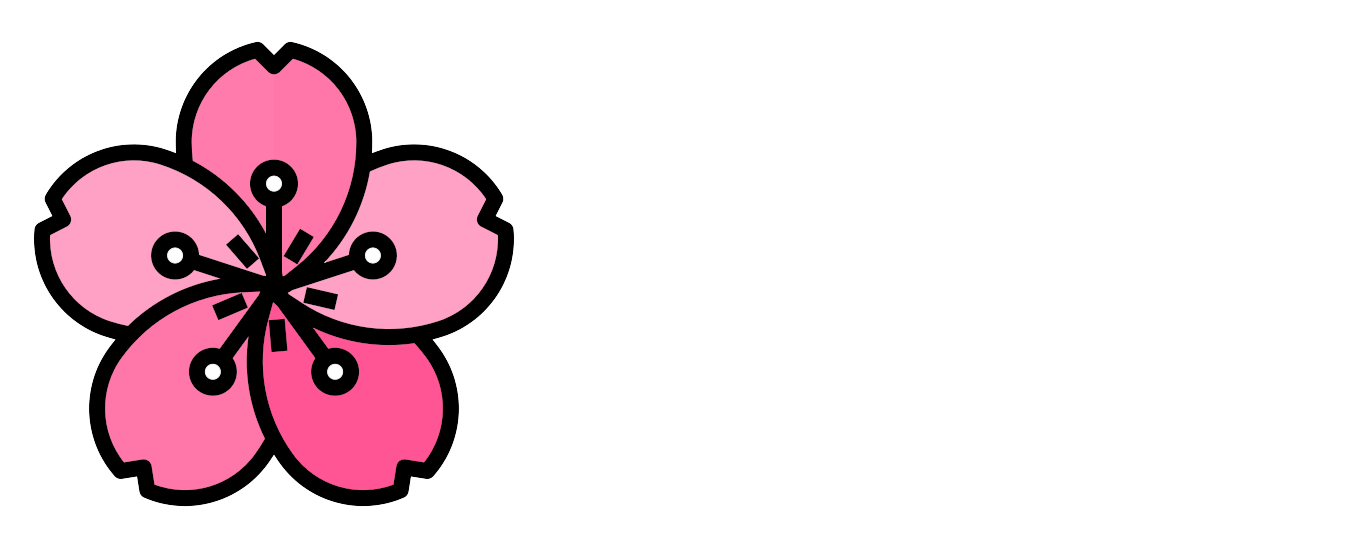一个不小的房间,这是男人的卧室。
这个男人21岁了,他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。看了看表,下午2:25。
还早呢。男人这样想着,不如来一把音游再走吧。——即便他已经知道自己手底下已经堆了干不完的活,这个自诩为90%的“J人”还是一如既往头也不回地将自己精心定制的计划束之高阁,打开了平板。
那块平板是去年夏天换的,上一块平板的死状历历在目,不过男人没有理会,因为他手里的这块平板业已伤痕累累:钢化膜从一角裂开,一条裂缝顺着一朵花纹顺流而下,在镜头边角画了一个三角形;屏幕中央偏下的特定位置,那里的疏油层已然脱落,即使是隔着钢化膜都能看到几个像是油手印的痕迹,好像和野兽近身缠斗过;屏幕边框更是惨不忍睹,一侧已经向下微微凹陷,使得屏幕和背板之间生出一道罅隙……
男人没有在乎这些,正如他起初向父母请求买平板时的动机是生产力那样,一切的一切都是对自己过去承诺和行动戏谑的奚落。就打一两把9的小歌1就走。男人想着,点亮屏幕,熟悉地跳过生产力页面来到最后一页,那里罗列着自己玩过的所有音游。打开Arcaea,男人的手指蠢蠢欲动。
要不打两首难的吧?男人似乎觉得自己状态不错,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新绿包2,看着自己F0C73的成绩,男人想着,不然今下午先试试能不能全连1首吧!
两点四十,男人打开了第一首歌,那首9+难度的歌曲。然而天不遂人愿,男人似乎总在某些相同的地方出错,有好几次眼看就要FR了,或者难点过了,却总在后面的某个不经意的点漏掉。
男人并没有注意时间,他只觉得暴躁。他扯着嗓子大吼起来,好像在咒骂谱师为什么写得这么难,又像在骂自己无能。
继续打,男人迟迟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成绩。越往后,他越暴躁,每逢一个漏击他都要把嗓子喊哑,用拳头哐哐猛捶平板,好像这是平板的错。音游就像一把钥匙,可以导引男人的心灵挣脱正常人的范畴,并打开一个名为“野兽”的开关。渐渐地,这个21岁的男人忘了时间,或者说不在乎时间——他已然决定,自己不打出像样的成绩就不走了,哪怕自己一开始只说小玩几把。
很快,男人起床一小时了,他知道自己早已经过了计划中要去自习室的点,但他还是磨蹭在卧室书桌前做着无用功。每逢不顺意,他就要像猩猩那样捶胸顿足、大吼着想要撕碎平板。
最后,几乎像他每次碰音游那样,他崩溃了。毫不意外,他把这块叙利亚战损版的平板掷了出去,平板的一角着地,做了一个后空翻,沉默不语的屏幕倒映出男人喘着粗气的脸,钢化膜上的裂痕又把男人的面庞撕成两半,像是案板上对切的小米辣。
很快,男人眉毛的倒八字变成了正八,极度的冲动之后,带来的是一种满溢着悲伤的扭曲痛苦,这种无法控制的痛苦将男人拉下万丈深渊,其中好似杂糅着冲动的悔恨、对自己无能的厌恶、打破计划的愧疚和对虐待平板的悲哀。一锅乱炖的混合汤汁刚刚出锅,便要整锅浇在男人头上,很快便把男人的情绪从顶峰扯至低谷。男人只感到一阵不受自控的脱力和来自心脏的悲鸣。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。几乎每次打过音游都是这样的结局——他到底做错什么了?起初不都是为了快乐吗?为何打至最后总要到这步田地呢?
有点太过火了。
男人捡回了平板,他望着这块屏幕,想起了上一块平板的惨状——大抵与现役的这块情况一致。一股冲动从心中升起,不过这次,好像有变化。
男人开了锁,还是跳过了生产力,来到了音游区。
不过这次,他按住了那个熟悉的图标。
“确定要卸载吗?”
……
做完这些,望着空荡荡的文件夹,男人松了口气。
他知道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音游,但,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次就此别过的勇气,哪怕是一阵子、一段时间——嗯,足够到冷静下来,足够到有时间自我反思,或许足够到找回别的爱好兴趣,譬如那个捧着书的自己,抑或那个握着钢笔的自己,还有骑在Gravel上的那个自己,哪怕是站在街机前的自己,也比冲着平板大吼大叫的这个自己要强得多了。
果断穿戴好衣服,拿起电脑和背包,男人走出了家门。时针指向3:40,距离男人起床已经一小时十分钟。锁上门,男人跳上了电动车。
男人突然想写点什么。他在路上风驰电掣,一边想着。不然题目就叫,所以我放弃了音游吧。
男人暗自点点头,走进了自习室,打开了电脑屏幕。
四点整,自习开始了。